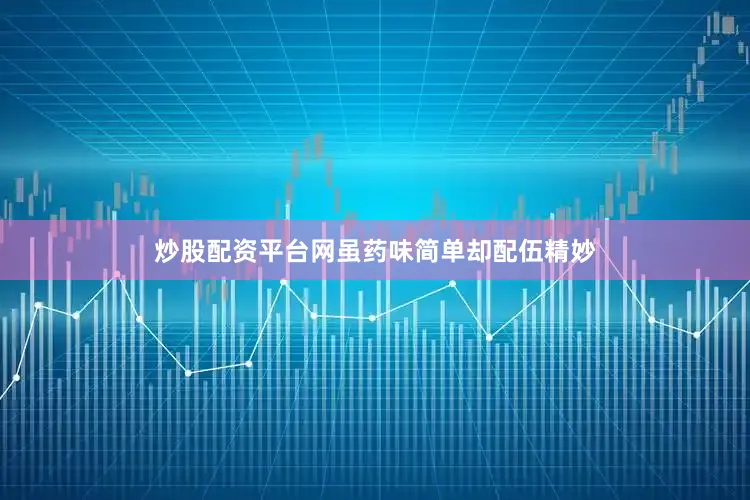文|荆谦谦
上世纪70年代末,我随妈妈返城,回到爸爸身边上小学。爸爸经常带上我,跨上那辆每遇到小颠簸时铃铛就自动抗议的自行车,去朋友家串门。我喜欢像鸟儿一样迎风而行的感觉,哪怕不得不忍受在大人堆里待上一两个小时的无所适从。
记忆中,有一个地方例外。那是王叔叔家。
他有个年龄跟我相仿的女儿,叫王念,有漂亮的丹凤眼和娴静的性情,更重要的是她有一把让我无比艳羡的小提琴,是王叔叔靠出书挣来的稿费买的。
我每次去,王念的妈妈总是热情地沏茶,端出瓜子和橘子招待我们,接着喊王念出来跟我玩儿。王念很矜持地陪我坐一会儿,不怎么说话,便借口有作业要写,只留下一个淑女的背影给怅然的我。
阿姨一边微笑着给我剥橘子,一边随口问些考试成绩、征文比赛的事儿。我对大人一成不变的问话往往觉得无聊,继而生出些许厌倦。我心里最盼望的是看看王念的小提琴,听她拉上一段随便什么琴声,哪怕里面出来的声音像爸爸自行车把上的铃铛那样磕磕绊绊,我也不会捂上耳朵,我会说,你拉得比上次好多了。
展开剩余67%但是,我没有说,我什么也没有说。爸爸说过,等他的书出版了,也给我买一把小提琴。我有点伤心地坐到爸爸旁边,听他跟王叔叔很兴奋地谈论李白和李清照,身为小学生的我如听天书,但我装作很有兴趣,装作很在行地竖着耳朵,来显示我比王念有学问,而且学问渊博得多。
爸爸从不主动教我古典诗词,更不把满屋子的古典文学书籍推荐给我读,哪怕是最浅显的《唐诗三百首》。他为我订阅了《儿童文学》和《少年文艺》,但常常教育我要学会一门扎扎实实的技能,譬如拿手术刀切掉异变或坏死的组织,再譬如设计一种不冒白烟的锅炉。
我从自己与那个时代共振的童年经历以及跟同学的比较中,像解数学试卷上的附加题一样,推算出了师出名门的才子不得其所的人生轨迹,而我的学习成绩出奇地好,作文比赛屡屡获奖。看着爸爸在熟人和亲戚面前掩饰不住的笑意,我深深地知道,在他的书问世之前,我是他隐匿的骄傲。
我没有小提琴,接触的唯一音乐是伴着老师的脚踏风琴或者手风琴从喉咙里发出的嘹亮歌声。我的歌唱得不赖,跑步像驼鹿一样矫健,跳绳、丢沙包、踢毽子样样都在行。
所以,一段时间过后,依照生活的逻辑,我就把小提琴的事儿给忘了。或许,一开始我只是出于小女孩的攀比和虚荣才生出拥有它的渴望,编织出万人瞩目的幻想。
而王念表现出的冷漠,也可能只是因为大人之间对孩子的比较造成了我和她之间不应有的隔阂。大概,不论大人还是小孩,都在不同程度地偷偷较劲儿,就像水往低处流的自然法则,悄无声息地穿行在人生的每一个角落。
我有时候在爸爸提到王叔叔时会想到王念,想到那把小提琴。更多的时候,想到爸爸像弥补童年的缺失陪伴一样给了我沉甸甸的爱,那些忧伤就变成阳光里的一滴水蒸发了。
我清楚地记得,离开王叔叔家,我变得怎样兴高采烈——爸爸又成了只属于我一个人的了!
我坐在他破旧的自行车横梁上,时时躲闪像刺一样故意扎得我脖颈有点疼的胡须。回家的路有段非常陡峭的下坡,他像踩风火轮般不停地蹬着踏板,好为随后的下冲蓄积力量。链条在脚下发出沙沙的急促呼吸,我感觉到爸爸像气泵一样的怦怦心跳。快到坡地起点的时候,他嘱咐我“坐好,要起飞喽”,然后,喉咙里涌出呜呜呜的一连串音乐般的长音,我们迎着呼啸的风,迎着扑面而来的尘土,俨然在飞翔。
我看见白云在蓝天上飞快地奔跑,一朵云甩开另一朵云,仿佛要追赶我们,接着又被前面更大的一朵云翻着跟头攀越过去。它们发出的脆亮笑声甚至感染了车把上像打嗝一样响个不停的铃铛。我伸出右手想摁住它,被它一蹦一跳地弹了回来。
这时,旁边疾速驶过的公共汽车刮来一股更大的风,乌云般黑压压的车厢里有人将手臂伸出窗外,在风中拉成一条笔直的弦,它掠向前方,和我们一起,去奔跑、去飞翔。
我仿佛听到了一首歌,一首哀怨的小提琴不曾拉出的歌。那最真实的声音,在我童年的心弦上从未停止过回响。
(作者为资深俄语翻译)
发布于:山东省保利配资-炒股配资公司站点门户-证券配资的条件-股票如何杠杆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